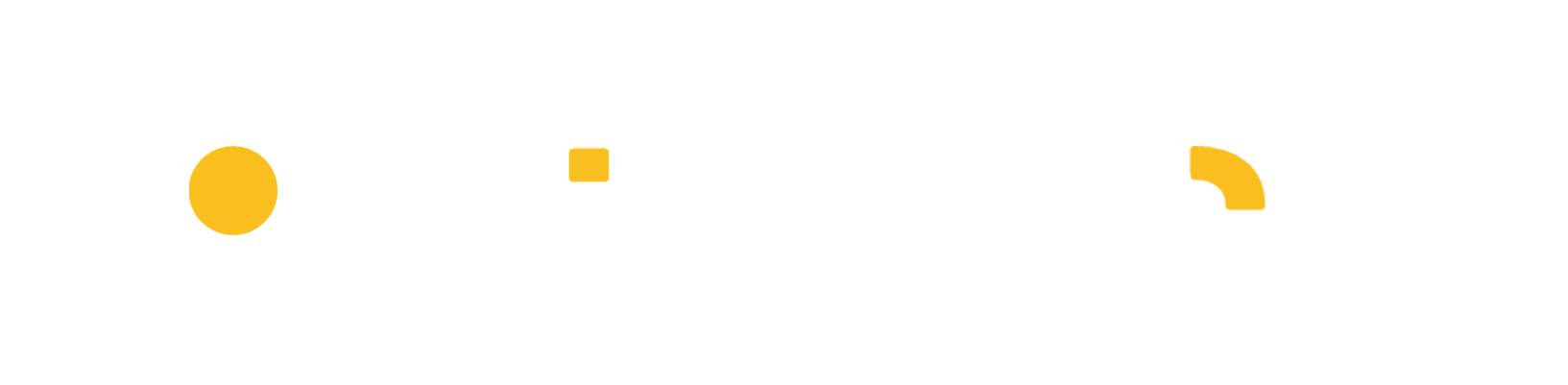对话Jordi Alexander:如何实现连续13年每年赚100%?
本次对话是Twitter Space的一次访谈,访谈对象是Jordi Alexander,作为Mantle战略顾问和Selini Capital的首席信息官(CIO),他参与了多个Crypto项目投资。
Jordi Alexander曾拒绝了Citadel(华尔街传奇投资人士Ken Griffin创建的全球做市商,公司拥有20年历史)的返聘邀请,选择去新加坡从事Crypto资产交易。他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价值500万美元的交易盈亏截图,还撰写关于Crypto资产博弈论的深度分析文章。
Jordi年轻时参加过国际象棋和桥牌国际赛事,常年入选全球综合智力竞赛榜单(该赛事全面考验战略思维能力),最近在2024年又斩获世界扑克系列赛金手链。作为Selini Capital的创始人,这家公司专注于Crypto资产的做市、自主交易和风险投资,在过去的13年里,实现了惊人的100%复合年增长率(CAGR),净资产每年翻倍。
本次对话篇幅较长,编者进行了修订和提炼,但依然有上万字,建议收藏阅读消化(加粗体为主持人问答)。
为什么选择从职业扑克手转为交易员?
你是从何时开始认真对待扑克的?
2003年上大学时正式开始认真玩扑克。当时正值“Moneymaker效应”巅峰期——他刚赢得世界扑克系列赛冠军,引发了全民热潮。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反复见证了这种现象:当某个领域成为“热钱聚集地”时,聪明的年轻人就能从中大赚一笔。如今,这个领域是Crypto资产;过去可能是扑克,再往前可能是每日梦幻体育联赛。这种“热钱球”总是在不断转移,而关键在于抓住机会并充分利用它。
扑克市场是否像其他市场那样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短期与长期的永恒辩证关系。短期来看,金融危机可能让一些人转向扑克,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从长期来看,扑克市场并没有像金融市场那样受到直接冲击。如果你足够热爱并坚持几十年,或许能成为像Doyle Brunson那样的传奇人物。但对我而言,扑克始终是一件我享受并充满热情的事。我热爱竞争,但从未想过将其作为毕生事业。不过,我确实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我立刻决定不再走华尔街的路线,而是搬去迈阿密专职打扑克。这个决定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我的母亲。她甚至羞于告诉朋友我是职业牌手,谎称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我格外珍惜那段岁月,那是我个人成长的爆发期。当你失去社会框架的约束,没有老板发号施令时,你必须学会自我管理。我开始驯服自负、控制情绪,这种生活对职业牌手来说异常艰难,尤其是像我这样成长过程中没有受过系统思维训练的人。当时我根本不懂建立收益电子表格、严格管理资金风险比例这些专业方法,纯粹靠着“我很擅长这个”的自信,盲目挑战任何级别的对手。
那段时期你对自己最大的认知突破是什么?
一方面,我在与顶尖选手(比如当时的Scott Seiver)对抗中建立了信心,证明自己足以匹敌最强者。但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缺乏情绪韧性。虽然我不会像新手那样情绪失控,但我必须学会处理波动、保持冷静。这个过程充满了情感冲击,想象你的生计完全依赖胜负,当遭遇连败月份又没有储蓄缓冲时,那种压力迫使你直面内心最深层的恐惧。这种经历让我更加了解自己,也让我在未来的交易和投资中更加从容。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优秀交易员都有打扑克经历,他们先在牌桌上解决了情绪管理问题,他们能够在扑克中摆脱失控的困扰。但我见过的最致命的错误莫过于:明明掌握优势,却因为一个小失误而情绪化操作,最终酿成大祸。在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愤怒中损失了50%的投资组合。
是的,心理学中有一种东西叫做对公正世界的信仰。有些人对公正世界有着非常强烈的信仰。我想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对公正世界的信仰意味着结果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被车撞了,你可能做错了什么,这是很多人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但在扑克游戏中,有时你显然做了正确的事情。你把钱投入到好的方面,但你还是输了。不可否认,从简单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不是一个公正的世界。这是行不通的。它训练你接受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当你做正确的事情而你无法控制随机性时,坏事也会发生,它基本上让你对随机性更加适应。
扑克中你只能押上台面的筹码,但交易中你可以押更多。通过杠杆,你可以押上全部筹码甚至更多,头寸规模空间比扑克大得多。
确实如此。在扑克中,你需要进行的凯利公式调整相对简单,因为你的最大损失仅限于台面上的筹码。但在交易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果你进行方向性交易,假设最坏情况下某标的会涨2倍,结果它却涨了10倍,此时你面对的概率分布可能完全超出凯利公式的适用范围。这意味着你需要更加谨慎地评估风险,并且时刻准备应对超出预期的市场波动。
你20多岁职业扑克生涯中经历过重大资金回撤吗?
唯一的一次大回撤发生在我分手后。那个阶段正是我的重塑期,需要在一个要求情绪绝对稳定的游戏中保持冷静,但现实生活却完全失衡。这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当时我根本不该继续打牌,结果我损失了80-90%的本金。我不顾风险去打超高额桌,遭遇重创后情绪失控,继续加码。其实从总体决策来看,并不算完全错误,但我选择的级别过高,导致波动必然带来这种结果。这次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情绪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重要性,也让我在未来的交易中更加谨慎。
当时的资金规模有多大?
大约40万美元。虽然不算巨额,但损失确实非常痛苦。那时我陷入了抑郁期:生活全面崩溃,长期恋情终结,财务保障也消失了。突然之间,我迷失了人生方向,毕竟投入数年的职业根本没有晋升通道,不存在“高级扑克玩家”的职位阶梯。那六个月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不过,这种至暗时刻往往具有破茧重生的力量。最终,这段经历反而成为了一种恩赐,让我得以直面成长过程中的诸多需求。你要么找到内心的平静与禅意,跨越障碍开始成长;要么就被困在原地。可惜很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平行时空里的我或许也会如此。所幸我有挚友的支持,或许内心也迸发出了某种韧性,让我最终走了出来。
2010年或2011年左右,这段经历成为了我人生的转折点。我最终决定:虽然扑克很有趣,但我要重返现实世界,不再局限于游戏。于是,我开始逐步扭转局面。当时我仍在进行大量的体育菠菜,专注于网球和篮球领域。那时相关软件还不发达,反应敏捷的人可以进行实时交易。我做了很多必发交易所的实时体育投注,这些经历后来成为了我简历上的亮点。我确信这增强了我的概率直觉,现在我能“看见”概率分布,就像有人看色谱一样直观,这种感知对我而言宛若天生的语言,这些能力主要是在那些年间构建的。
从扑克牌玩家到交易员学到了什么?
2011年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申请了MBA。我考上了顶尖学校,他们录取了一名职业赌徒,这很不寻常,因为其他人都是BCG顾问之类的。我考上了新加坡的一所一年制学校。我上的是一所叫INSEAD的学校,这是一所非常好的MBA学校,我通过与所有这些专业金融人士和专业企业家打交道积累了经验。我回到了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学习,看看外面的人都在做什么。
申请商学院时,你是否在个人陈述中提到扑克和其他博弈游戏经历?
我确实提到了这些经历。商学院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在文书中解释扑克训练将如何助力我的未来事业。当时,我并没有想成为交易员,而是计划从事战略咨询类工作,认为策略思维是两者的共通点。然而,毕业后在面试时,我发现那些公司根本不愿意录用我这种穿T恤的非正统人士,他们只想要西装革履的标准员工。
我唯一收到的录用通知都来自对冲基金。交易是当时仅有的选择。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想当交易员,觉得这和之前的生活过于相似,又要回到终日坐在桌前玩游戏的状态。我渴望做些更具创业精神的事,但现实是只有交易岗愿意接纳我。他们钟爱扑克玩家,认为这是能力的一种信号。
就在那时我读到《市场奇才》。当时有家大型对冲基金的负责人约我喝咖啡,他说:“看,你的背景很特别,我能看出你天生是交易员。读读这本书吧。”然后把自己的《市场奇才》送给了我。阅读后,我意识到这确实与我的技能组合高度契合。
那时我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一名交易员。不过,我最终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没有接受他的工作,也就是自由选择做多做空,而是选择了一份高频交易(HFT)的工作,并搬到了伦敦,这很奇怪,因为我没有编程经验,也没有量化方面的任何经验。在HFT中,你需要具备两点条件。你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程序员,并且你需要非常擅长统计。
我总体上擅长数学,但经过多年打扑克之后,能够在任何游戏问题和逻辑谜题上表现良好的面试能力让我仍然获得了这个职位。我只是说,看,一切都变得更加算法化。我要么停留在过去,做一些自由选择的事情,要么尝试走向未来。因此我接受了算法交易的角色。
所以你试图更具有前瞻性,不仅仅是成为对冲基金的自由交易员。你想做一些更具前瞻性的事情。
我认为2012年这个领域仍然非常有吸引力且处于鼎盛时期。我的意思是,当时到处都在印钞。当时,没有多少公司。所以即使你在这个领域里有点笨拙,你仍然能在牌桌上占据少数几个席位之一。这很疯狂,因为我加入了当时仍然是世界顶级的公司Getco。这是在他们与Knight合并之前,然后最终与virtu合并等等。所以他们不再存在了。但当时,他们拥有顶尖的技术。我记得我第一天上班,老板让我做一个欧元兑美元的模型。你可以输入任何你想要的参数。它会赚钱。不管你做什么,它都会赚钱。基本上你可以制作最愚蠢的模型,它仍然会赚钱,因为技术如此优秀和快速,你总是有优势。所以,果然我投入了一些东西,它每天赚了一百美元左右。
我当时确实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在加入之前,有人告诉我,这是个工作机会,你有两个月的时间加入,你应该学习Python,所以我就上网学习Python, 并试着做一些练习之类的东西。但我的水平还很差,我不得不找到其他方式来做出贡献,因为我不会成为那种编写所有这些东西的人。
值得庆幸的是,我存在的理由是,HFT中的所有这些人都非常优秀。他们擅长编码和技术,但他们对市场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不是正在关注的事情。我刚刚开始发现所有这些非常基本的改进。其中一些秘密我应该保密。我没有意识到发现它们有多难,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太明显了。
那几年欧洲市场尤其精彩。
那几年确实非常精彩,尤其是德拉吉推行了许多激进政策。我们作为新生团队表现非常出色——首年就实现了八位数的盈利(多数团队难以开局如此顺利)。我在那里的两年间,团队持续爆发式增长,我的模型也贡献显著。但当时我并不是组合经理,这迫使我面临一个职业抉择:是冒险自立门户,还是加入成熟机构?这个决定令人忐忑,毕竟我仍然缺乏编程的硬技能。
所以你自己创立了高频交易公司?
并没有真正创办公司,而是以合伙人身份加入了一家小型机构。两位创始人中有一位与我的理念高度契合——他虽不懂交易,但技术水平远超我在Tower或任何地方见过的开发者。他简直是技术奇才,而我则擅长另一维度。这种组合能让我们达到世界级水准,因为单独行动都难成气候,但合作就能产生质变。于是我加入了这个约15人的小团队,当时他们主要交易石油相关品种和零散品种。我们花了六个月共同搭建的系统,如今已成为Selini资本的基石。那时已经编写了大量代码,构建了基础设施。所以严格来说,并不是我独立创业,当时我还没完全准备好。更像是组建自己的团队,在承担重大责任的同时,还不算真正运营公司——我觉得自己尚未具备那种能力。
当时你多大?
即将满32岁。
怎么进入Crypto资产领域的?
Crypto资产何时进入你的视野?
最初接触Crypto资产是因为公司在湾区,这是个极其特殊的地方,仅仅因为合伙人居住于此,我也就搬了过去(并不介意)。这里是2016年全球唯一能在咖啡馆随机听到人们谈论Crypto资产的所在。当时BTC价格约1000美元,我记得觉得太贵,转而买了些看似便宜的以太坊。后来做了首笔原生Crypto交易:意识到LTC会暴涨(当时才几美元),基于“散户单位偏好”的判断大量买入,最终在疯涨至250美元时抛售。当时周围有些朋友运营着首批Crypto对冲基金,规模虽小但给了我最初的市场启蒙。
你最初对Crypto资产有何看法?
2013年BTC上新闻时就有所耳闻,经历过小规模行情。当时在交易台读彭博社报道,觉得成为基础货币难度太大——黄金或许合理,但要全球突然共识将其作为财富储存手段,实在太牵强。2013年没买,2016年态度转暖:其他通证的出现让我适应了投机属性,但当时仍未将BTC视为价值存储。
当时对法币的普遍共识如何?
显然我们处于低利率的人造环境中,但人们只求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那时交易所经常莫名其妙地丢失订单,简直就是狂野西部,尤其是早年更为混乱。交易所会搞砸订单追踪,整个系统混乱到癫狂。和现在的专业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只是兼职参与,且被要求不能投入过多精力。所以只能说对市场有所熟悉,但并未全情投入。
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转向Crypto领域?
部分原因在于固收交易实在太过顺利,转移注意力将面临巨大的机会成本。无数个深夜我辗转反侧:是否该全力转战Crypto领域?但当时的成本实在太高。现在回想起来,真希望当初能更早入场,可那些年终究被虚掷了。2018、2019年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庆幸没放弃原有领域转投看似垂死的Crypto市场。但直到2020年,我才真正开始认真对待Crypto领域。
听来你此前主要在防守端运用市场认知(做市),直到后期才在进攻端(自主交易)发力?
自主交易的发展历程确实很有趣。正如之前所说,初入高频交易时,我就尝试将主观策略叠加到算法中,虽然公司并不鼓励这种行为。但后来我用实际业绩说服了他们——当策略持续奏效时,他们只能接受。事实上,二十多岁时最让我兴奋的是成为宏观交易员。记得我曾熬夜研读各种博客,某个华尔街绿洲论坛的博主谈论宏观策略时,那种捕捉亚洲时段行情波动的前瞻性视角令我着迷。相比之下,高频交易就像每天重复执行百万次赚取几美分的算法——虽然稳定,却乏味。
后来如何转向宏观交易?
我开始从交易平台利润中抽取部分资金,单独开设账户进行宏观押注:债券方向性交易、股指多空操作等等。有次非农数据公布时行情剧烈反转,我的特别账户单日亏损10万美元,这对习惯高频交易稳定盈利的我冲击极大。其他合伙人对此颇有微词,但我坚持用利润分成部分操作,并控制风险敞口。虽然环境充满阻力,但我觉得自己正在突破某种瓶颈,这种成长感推动着我持续加码。2016年小试牛刀,2017年扩大规模,2018年单笔波动达数十万美元,2019年跃升至五十万美元级别,2020年完全崩盘。
市场验证了你将自主交易与高频系统策略结合的正确性,公司内部的质疑声也减弱了?
绝对如此。当时所有人只求生存。所幸我们挺过来了,全年业绩优异。多数幸存的高频交易公司2020年都创下记录——挺过三月的机构在后三个季度获得极佳资金流,虽然难以解释但事实如此。不过我在自主交易上犯了错误,回吐了约10万美元利润,虽不影响全年佳绩但令人不快。我误判了高风险债券走势——当全球经济崩盘时,高收益债券理应贬值(企业偿债风险暴增),但实际却并不是。
微观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游戏。
它像是个非常细分的领域,虽然不如长期持有大额头寸那般引人注目,但重要性不容小觑。观察当今Crypto领域,每个试图生存的DEX(去中心化交易所)都在重构微观结构。无论是GMX的预言机模型,还是Hyperliquid的混合金库与AMM(自动做市商)机制。微观结构决定一切:它塑造参与者间的平衡关系,确保价格发现机制不会沦为掠夺工具,并培育出良性互动的生态系统。尽管Hyperliquid目前面临挑战,但其团队的高频交易背景赋予他们独特优势——相比其他DEX,他们对微观结构的理解显然更胜一筹。
将高频交易与自主交易结合始终合乎逻辑,但高频交易与创投的组合在传统金融界难以想象。
但在Crypto领域,由于做市交易的特殊性和项目方对流动性的渴求,这变成了全新的游戏。不仅如此,你对Crypto创投本身(比如项目本质)也有深刻认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Crypto世界大多围绕通证交换的基础设施构建。若深究第一层网络(L1)的本质,无非是创造通证并让人们通过某些DEX交易这些资产。而交易经验恰恰能帮助你评估项目是否真正为资产交换者创造价值,是否促进资本形成与价格发现。
如何看待Crypto资产的未来?
自2022年以来,Crypto领域的赌场论调愈发盛行。你如何将其融入长期愿景?
由于我的成长背景(长期浸淫真实赌场),这两种特质的交织令我倍感亲切。我确实认为随着美国政府持有BTC等趋势,机构化因素将日益重要。这完全合理,但我也乐于身处前沿同时观察两面。
你如何看待Crypto资产市场未来几年的演变?
整体市场遵循“愚我一次,其错在人;愚我两次,其错在我”的规律。市场永远渴求新庞氏游戏。例如本轮周期未出现NFT热潮——人们尝试过但未能复制成功。随后转向MEME叙事,编造流动性更强的故事。或许这次能成功?但目前看来可能并未奏效。
某些变革必将到来,我们会再次见证狂热。但形式必将进化,不会简单重复。人们需要相信致富神话,这种集体信念驱动着反射性循环。因此我认为我们将见证更多游戏化周期,只是形式不再雷同。
我认为最终可能是人工智能海啸将席卷整个世界。我确实感觉自己正站在水位不断上涨的高峰,但浪潮蔓延到我的位置尚需时日。我大脑中运用的能力类型,并非那种容易通过数据训练复制的模式。特别是在当下,我会说自己更多采用混合策略——多种alpha生成方式的结合。这里的alpha不只是单纯下单交易,更包括运营业务和创造附加值。我的方法论与知识结构过于专精,难以训练出通用模型,因此个人并不担忧。
合理。尽管在宏观尺度上你刚四十出头正值壮年,但相较Crypto市场参与者(年龄普遍集中在25-35岁),你已是资深前辈。是什么成就了你的长青?
核心在于自然积累的知识模块化。经过多年沉淀,我已将海量认知与模式识别能力封装成即用型思维框架。当遇到新情境时,能瞬间调用这些预装模块快速反应。这是巨大的竞争优势——我刻意构建了这种能力体系。记得十年前初听达利欧演讲时,觉得他智商平平、反应迟缓,后来才领悟到硬件与软件的区别:人类硬件指原始智商,软件则是思维决策系统。我自认硬件尚可,但更愿效仿达利欧般打磨软件系统。如何优化这套软件?答案是通过长期投资锤炼最佳判断力。判断力是种普适价值,无论世局如何变迁都弥足珍贵。AI唯有在判断力层面取得突破才能真正改变世界,而这恰是最难攻克的领域。
你经历过最糟糕的交易是什么?
2020年从传统金融转战Crypto领域后,最惨痛的交易是2020年底做空。当时这些另类资产已暴涨10倍,我觉得Cardano和DOGE这类项目纯粹是垃圾。传统金融市场至少存在人们认可的公允价值锚点,交易围绕这个中枢波动。但在另类资产世界,我付出了惨痛代价才明白:这里根本没有公允价值,只有动量效应与赤裸裸的贪婪。我曾天真认为3倍涨幅就会引发抛售,结果发现玩家们的胃口远超预期。我在0.015美元到0.005美元区间多次做空DOGE,直到某天马斯克突然站台——价格飙升至10美分时,我承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你是否注意到,越是冷清时期,另类资产市场越爱玩这种猎杀空头的把戏?
没错,这就像现在Hyperliquid平台上有人试图操纵市场。全球无数聪明人都在盯着Crypto市场——对那些想要独立赚钱且心智坚韧的人来说,这是绝佳战场。他们总能发现结构性的有利点位,不管他们是否愿意称之为“高胜率交易策略”(暗指Avi Eisenhower的手法)。就像你说的,无论是轧空还是其他把戏,冷清市况下人们必须扩大狩猎范围才能获利。
另类资产市场参与者类型单一,导致特定资产在特定场景下极易形成拥挤交易,进而遭到精准猎杀。讽刺的是,做空难度过高反而导致价格虚高,最终又催生做空机会。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当所有人都觉得“钱太好赚”,因为标的明显高估时,大量资金涌入做空,结果又形成新的拥挤仓位。叠加资金费率转负等诡异现象,使得永续合约市场(相较定期合约)成为最具博弈趣味的领域。更独特的是,这里没有追加保证金流程,你的账户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瞬间爆仓。
Crypto市场的生命周期也快得多。
是的,一切都被加速。由于做空机制匮乏,泡沫往往膨胀到离谱。市场上充斥着无脑资金:有人在另类资产见顶时接盘;特朗普通证刚推出就被炒到700-800亿美元估值,这些人根本不看价格,就像扑克桌上拿杂牌跟注河牌的赌徒——你甚至想不通他们哪来的钱。这种玩家群体随时间推移会被逐步清洗,但总有人从沙发缝里抠出钱来继续送人头。整个市场呈现出专业玩家与低效生态共存的怪异图景。
有哪些交易经验分享?
对想要精进的交易者,你有什么建议?
核心是心理建设。这对任何领域都适用,但对交易者尤其关键。若被自负情绪遮蔽判断力,你将寸步难行——而几乎所有人都会犯这个错误。很多人把自我认同与特定交易方式深度绑定,但要达到世界级水准,必须做到判断毫无杂念。这通常需要:
1.彻底放下自尊心
2.重构思维底层逻辑
3.坦然接受自身优劣
这个过程或许需要数年,取决于你处在心理进化的哪个阶段。对有些人来说,这更容易。但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我想告诉他们,看,我能看到你的自信与你所做的每件事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放下一切。就像我愿意从零开始,让你的自我接受一小段时间什么都没有,然后重建得更好。你可以很快重建,但你必须从坚实的基础开始。对我来说,克服一些挑战,我有很多自我怀疑。有人称之为“冒名顶替综合症”综合症。 我们认识的许多顶尖交易员,我与他们交谈过,其中不少人甚至至今仍受“冒名顶替综合症”困扰,尽管他们已是交易界的传奇。
我认为这很正常。某种意义上,这比毫无自我怀疑的健康。因为怀疑能促使你挑战自我:是否真正优秀?是否已具备所需素质?是否需要精进?存在自我怀疑完全合理。我认为“神级境界”是彻底摆脱这种状态。我不认为冒名顶替综合症是终点,去年之前我也长期受此困扰。
去年才摆脱?真的吗?
是的,大约在赢得WSOP手链、完成人生清单最后几项时,我才真正感觉:好吧,或许现在我真有两把刷子了。终于摆脱了冒充者心态。这种解脱带来了全新境界——不必背负自我怀疑,能以自信且谦逊的姿态应对挑战。我厌恶Crypto圈某些年轻创始人的做派:20多岁取得些成功(有时是疯狂敛财),就变得傲慢自大。你们肯定能想到具体案例——比如某些创始人发通证暴涨后,自以为无所不能,整个人格都扭曲了。这种膨胀终将导致陨落。太多创始人因数字上涨就把自我价值与之绑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将永远保持谦逊,绝不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存在。这种根基意识对持续成长至关重要。
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必须避免“一击成名”综合症。
是的,太多人昙花一现后就幻想能无限复制成功。或许专注耕耘能延续辉煌,但年轻人突然暴富往往不得善终。我有个比喻:交易本质是种心理治疗。 你必须校准世界观才能持续盈利,容不得半点偏见。
这是我最爱交易的原因。 这不是靠喊多就能赢的游戏,而是最公平的竞技场——你的出身人脉毫无意义。当身处订单簿战场,真相自会显现。
你认为自己的交易理念有何独特之处?
我的核心是风险回报比架构。其他人有各自提取阿尔法的方式,而我脑中始终运行着概率分布模型。前几天我们讨论过这点——我通常不持仓过夜,喜欢清空头寸保持思维清爽,待时机成熟再出手,结束后继续休整。我构建的是滚动式仓位分布通过风险回报比架构提取阿尔法。
我会逐步加仓,直至触及最大仓位限制。这个上限的设定基于极端风险情景——即使发生灾难性错误,损失也不会超过可承受范围。然后围绕这个风险回报比动态调整仓位规模。这就是我从市场中提取阿尔法的核心方法。
当然,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平衡风险回报比。你需要综合考量五到十个维度:比如不同时间周期买方的成本基准。过去我对此极为擅长——高频交易时期整天坐在屏幕前,除了盯着图表别无他事。这让我练就了极强日内交易能力,能在分钟级窗口内判断后续数小时的风险回报比并精准操作。
2021年我面临重大职业抉择。
当时有两个选择:如果全年专注交易,预计能赚取1亿美元利润(基于当时单位时间盈利能力的合理估算);或者只投入10%精力交易,剩余时间创立高频交易公司,构建具有长期价值的事业体。这是个艰难决定——短期暴利唾手可得,但不确定性中孕育着更持久的可能。
最终我选择了后者。真正吸引我的是组建团队、共同成长的创业体验。如今看来这步走对了。虽然2021年本可赚得更多,但绝不会收获现在这般丰沛的满足感。
你还提到“净值增长天花板”机制?
是的,我始终将年度净值增长上限设为3倍。当超额达成目标时,剩余精力会转向自我升级。就像扑克玩家首年赚10万,次年冲到25万后选择停赛进修——这是为下一次飞跃筑基。从交易生涯伊始,我就执行这套“年化2倍”法则,13年来始终如一。
每年真能实现净资产翻倍?
当然会有波动,有些年1.5倍,有些年2.6倍,但长期复合增长率维持在这个区间。可持续的秘诀在于:当收益超预期时,将脑力资源转向能力建设而非继续逐利。就像扑克选手在盈利期主动停赛,专注研究新策略。这种自我训练机制使我保持进化弹性。
人们本能地厌恶下行轨迹。比如去年给某人发的奖金减少了,即便总额更高,对方仍会感到不适。他们宁可第一年赚10万、次年20万、第三年30万,也不愿首年80万次年却跌至20万,虽然总金额更多,但轨迹下行会引发“是否走错方向”的焦虑。这种心理机制根植于原始猿类本能,我们对逆向发展有天生的排斥。
这非常有趣。你似乎在避免损益表(P&L)的崩盘式波动。当达到某个里程碑后,开始更多为长期目标优化——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自身幸福感。
观察Ken Griffin(虽未私交)这类人物的职业轨迹,他们总在铺垫下一阶段,进程看似缓慢,但十年后蓦然回首已跃升数阶。我自身也印证了这点:每年都感觉对世界的影响力在自然生长,甚至无需刻意作为。我享受这种有机渐进的成长,远胜于追求一夜爆红。
你认为职业发展中必然存在四年左右的低谷期吗?
从数学角度看,显然在某个时候你必须这样做,对吧?我认为按照这种运行速度我还能再维持几年,也许这种速度就不再可持续了。
值得庆幸的是,Selini,我创立的公司,目前拥有许多不同的部门,有些部门在不同的年份表现优异,有些部门表现不佳。显然,如果整个Crypto资产市场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适应并转向TradFi。但即使是那扇门,我们也敞开着。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不太担心。如果你开始在增长中建立韧性,那就没问题了。
我曾误判学习曲线,原以为40岁将停止学习,我以为我脑子里会有一个心理参考,比如我认为自己处于学习曲线的哪个位置。我当时的学习进度是92%,然后我觉得明年我的学习进度是95%。现在我的学习进度是97%。我只是估计,到40岁时,我就会完成,不会再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现在只是执行。然后,当我39岁时,我从我认为的95上升到了102。然后你意识到它实际上不是满分100,因为它没有意义。你恰好有102。然后它实际上可能在500左右。你只是离目标还很远,距离知道的东西还很远,还有更多的东西。所以我最终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40岁之后,我需要学习和成长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以为我只需要执行,但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都在学习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的东西。
我认为成长的心态最终会让你感觉自己已经达到顶峰。这就是我们说过的,你不想感觉你最好的岁月已经过去了,现在你只需要适应你退休后的生活。幸运的是,世界上有这样的例子,人们可以一直努力工作到老年。就像沃伦·巴菲特一样,永远不会达到顶峰。
似乎你会同意自我控制可能是人类经历中最有趣的游戏?
十分同意。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信息之目的,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如有侵权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络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早报 | Lighter 24 小时交易量突破 110 亿美元;Circle Q3 财报公布;Strategy 美股市值跌破其 BTC 持仓价值
整理:ChainCatcher 重要资讯: 币安将停止币安直播平台服务,币安广场将继续提供直播服务...
24H热门币种与要闻 | Sui将推出原生稳定币USDsui;美SEC拟推出基于Howey测试的代币分类法(11月13日)
1、CEX 热门币种 CEX 成交额 Top 10 及 24 小时涨跌幅: BNB -0.78%...
区块链骑士
文章数量
265粉丝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