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湧現:為什么DAO將崛起?
原文作者: 唐晗
原文來源: The SeeDAO
已經有不少組織开始採取 DAO 的方式運轉,但更多的人則抱着懷疑的態度:這種組織結構可能長久嗎?它在經濟上可持續嗎?“效率”低下、流動性極高的 DAO 可能取代公司制嗎?
面對這些懷疑,我試圖從另一個視角——湧現——來解釋為什么 DAO 必將崛起,並成為接下來這個時代最不可忽視的組織制度。
什么的效率?
效率永遠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目的。 高效的世界應該讓人人直達目的,實現他們真實的愿望,而不是生活在種種顛倒中。許多人盛贊公司制的高效性,往往是就其協作實現某一大型工程而言。例如:蘋果的生產线。然而,如果我們追問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這種制度是否讓制度內的個人實現了自己的真實愿望?它真的幫助人們生活的幸福了嗎?答案則往往是否定的。生活在現代公司制裏的人通常苦不堪言。為了養家糊口,從事與自己真實興趣無關的事情是常態,這個自不必說;糟糕的是,現代公司系統已將生產產品的工序拆分到極其細致的地步,讓每個參與者都成了某道工業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無論是工廠中的工人,還是前端程序員,還是新媒體排版員,都是如此。人的位置被固定在了一個個可以隨時被整體拋棄的崗位中。在這樣的系統中,作為螺絲釘的員工很難有什么選擇,或者讓自己獲得強烈的成就感。他們的任務乃是讓這條流水线在不出差錯的情況下持續運作,而不是綻放自我。

圖片來自 Ern Gan on Unsplash
甚至,對於這樣的流水线體系而言,強烈的自我綻放往往意味着麻煩。即便個人的自我綻放可能在短期內為公司帶來收益,但它也預示了個人的不可替代性和系統的脆弱性。個人的出走可能會讓這個系統一夜坍塌,因而不得不防。資本由此展开的種種博弈令人感到痛苦,此處的例子(如李子柒)不消勝記。——總之,這不是一個天生放大個人潛能,鼓勵每個人自我湧現的系統,且往往有壓抑個人,要求人們為了某個集體目標(基本是錢的目標)而犧牲之實。
公司制造成了老板與員工的對立,這通常還會跟另一個詞語聯系在一起,那就是“剝削”。在這種體系中,員工的工作是層層向上負責的。即便再开明的人,如果他的位置被放在了老板的位置,也不得不以利潤為導向,依靠層層管理的方式來安排公司運轉。
以我個人為例:SeeDAO 的前身是一家名為 CryptoC 的公司,而我是這家公司的老板。首先,這家公司的員工基本是從社區中發現優秀份子收集而來;其次,我嘗試以像 DAO 這樣的民主方式來讓員工對公司的發展提出意見,大家甚至可以直接在公司當面對我進行群體抨擊。然而,當 SeeDAO 誕生後,我還是發現了 DAO 成員與公司員工之間的劇烈衝突。
無論公司內多么民主,運營 DAO 的員工的第一想法是對老板負責,實行向上管理——因為他們的工作由老板提供,從老板那裏拿錢;而不是像社區成員那樣完全站在社區立場思考問題。一件殘酷的事情擺在了大家面前:公司畢竟是公司,不是 DAO;老板畢竟是老板,無論老板多么开明,他就是那個掌控了員工生殺大權(包括工資升降,是否還留在公司裏)的人。員工真的很難跟老板做朋友。
公司沒法把錢拿出來給衆人投票決策,沒法說員工的去留讓員工自己投票。在這種框架下,所謂的民主是有限的,甚至是虛僞的。在 CryptoC 運營 SeeDAO 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2023 年 2 月份,SeeDAO 某些社區成員的能力已經超過公司員工,他們對 CryptoC 這家公司的運營方案感到不滿,站在社區的立場提出訴求,抨擊 CryptoC 公司本身,要求對社區進行改革。在這件事情上,當我和白魚選擇站在社區成員那邊時,公司員工會反過來感到委屈和不解。“你以為你依靠的是誰?是公司裏的員工還是社區成員?”在他們看來,直接從我這裏拿錢做事的員工顯然比高流動性缺乏忠誠度的社區成員更可靠——沒有公司員工,我的想法和命令無法落地;而如果沒有某個社區成員,通過活動總還是能吸引到下一批的。我對他們的想法感到詫異。這件事讓我开始反思由錢控制的關系、中心化之惡和真正的效率。
2023 年 2 月份,我已經親眼見證了 SeeDAO 社區成員湧現的效率。我感受到了真正在社區中指認到自己生命價值的社區成員做事的激情,這和在公司裏一邊做事一邊向上管理,每天尋思着如何從老板那裏得到更多的錢與福利的員工之間有天壤之別。在公司裏,我做老板也痛苦,員工做員工也痛苦,這件事最終的解決方案以我解散 CryptoC 這家公司,把所有的融資款打到 SeeDAO 金庫,开啓全面的 DAO 治理而告終。我終於可以不做老板,錢的流向可以付諸公議而在社區裏獲得合法性,人們需要對社區負責而不是對我負責,這是目前我最慶幸的事情。若非如此,以 SeeDAO 在 2022 年所融到的資金,絕無可能度過這一輪漫長的熊市。不過這是後話了。
繼續談論公司制。公司制在效率上最大的惡是對人的消磨。人們對公司的印象是用勞動力換錢,是一個單純的“我給你賣命你給我錢”的金錢交換關系和控制奴役關系。“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躺平論”“ 996 反壓迫論”“上班摸魚嫖資本家論”都應證了這樣一個事實:現代公司裏的工作普遍是痛苦的,具有被迫性質的,是不情愿的。如有可能,人們其實根本不想這樣生活。
那么在我看來,在實現一個終極的社會目標——創造一個令人幸福,且具有意義感的社會上,公司制是低效的。 公司制本來是為了解決人們基本生活問題的手段,在保障了社會基本的物質供應後,我們本該回到真正的目的——幸福(這裏面顯然包含了關懷別人)上,但如今公司制的目的——資本的增值,卻實現了對終極目標的僭越。追求無止盡的錢,反過來成為了催眠人類心靈的魔咒,就算它要求我們踐踏、欺詐、殺戮他人(這些都是離幸福越來越遠的方向),人們也會照做。但這種魔咒畢竟不是真實,社會無處不在的痛苦——焦慮、絕望、無意義感、扭曲感、抑鬱等,都在提醒我們這一點。
此外, 在實現一個終極的個人目標——發現並成為自己這件事上,公司制對大多數人也是低效的。 公司制往往遮蔽了我們,扭曲了我們,規訓了我們,抑制了我們。我們每個人心中本來都有自己的”道“,都有自己的本來面目和人生使命,但這些事情在公司面前變得一文不值。一個詩人被變成了一個文員或是一個銷售,一個喜歡和家人待在一起的人不得不忍受無止盡的出差,一個喜歡做遊戲的程序員卻被安排了破壞身體的 996 工作壓榨。——人們沒有選擇,無法展开自己的”內在道路“,使他們的靈魂在深處鬱鬱而終,或是日日悲鳴。
失業大軍與抑鬱大軍
人不愿意在流水线化的公司裏工作,並不代表人不愿意工作。與其他動物不同,單純的喫喝拉撒滿足不了人類,掌握了語言和工具的人生活在一個又一個事件裏,人類在認識和理解世界的過程中,天然就生起了創造和行動的衝動和意愿。有人將其稱為“勞動”“實踐”“創造”,我姑且將其簡稱為“作”吧。
欣賞一首歌、寫一首詩、做一把椅子、治療好一個病人、愛一個人……這些都是“作”。人通過參與一個又一個的事件完成了自己的社會化,建立與他人的連接,並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義。如果完全把“作”拿掉,我們可能很難想象什么是人類的生活,甚至什么是人類。
然而,在資本主義體系下,“作”的導向是金錢,其細胞單位正是公司。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愈演愈烈的貧富差距,資本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資本越是在少數人手中,多數人的消費就越不充足。消費動力不足,經濟增速就越是緩慢,市場競爭就愈發激烈,公司之間的內卷就越發殘酷。這種內卷傳導到公司內部,就是裁員和員工之間的內卷。
失業大軍與日俱增。這一點在 Covid-19 之後日益明顯。關於這個話題,B 站上曾有一個一夜爆火的視頻,講的是中國傳媒大學的碩士和華中師範大學的大學生畢業五年積蓄 3000 元,如今在火鍋店做保潔的故事。在豆瓣上有一個“輕體力勞動者小組”。有一群大學畢業生聚集在這個小組裏,聲稱不愿意再從事任何內卷式的腦力勞動,而愿意從事類似於保潔這種輕體力勞動,緩解他們的精神痛苦和身體痛苦。(因為輕體力勞動可以馬上看到勞動成果,並且不需要去想很復雜的事情,還可以讓頸椎得到鍛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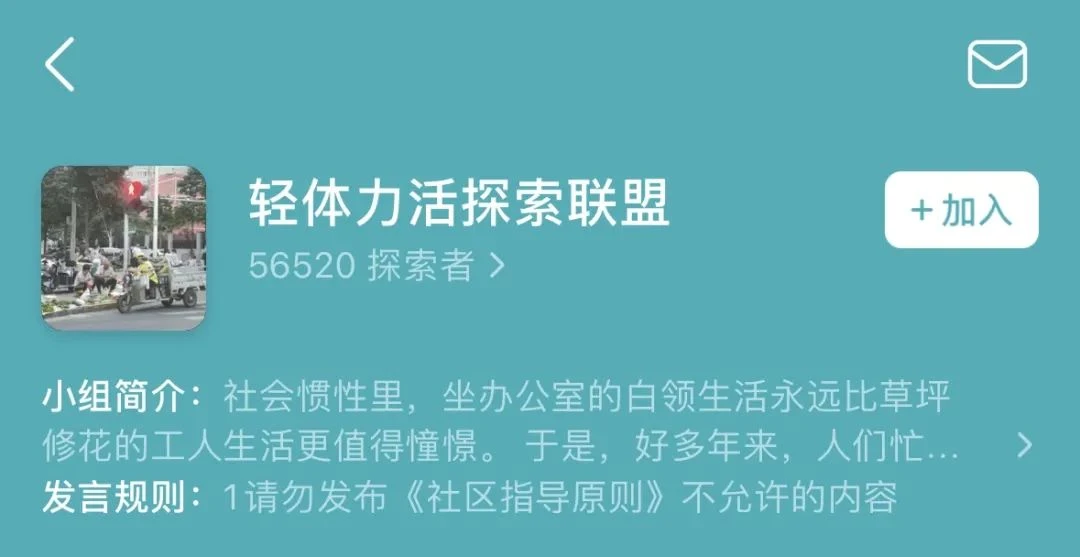
根據中國政府在 7 月 17 日公布的數據,今年 6 月中國 16 到 24 歲青年的失業率為 21.3% ,每五個青年裏就有一個人無事可做,但實際這個數字可能更高。中國不是個例。如今資本主義已經席卷全球,各國經濟連為一體。我在周遊世界時發現,高失業率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危機——全球的失業青年們都看不到未來的出路。
伴隨着失業大軍的是可怕的抑鬱大軍。在科技如此發達、高等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令青年們難以接受的事情是寒窗苦讀十幾年,最後的結局是回家啃老。我在上海疫情的時候發現,在人們尚有積蓄的情況下,失業給人們帶來最大的焦慮不是沒錢生存,而是與社會斷連。失去了“作”的機會,職業技能和社交關系在失業中慢慢荒廢,讓原本生活在正常軌道中的人們對自己失去了信心。這種自卑進而引發了人對未來的焦慮,變成了失眠和抑鬱。我意識到,雖然金錢的回報十分重要,但工作的意義遠大於金錢。工作關乎於人的尊嚴,以及人對自己和對社會的看法。
事實上,SeeDAO 擴張最快的時候,正是在上海疫情封城的時候。那時候,不少互聯網行業從業者陷入了失業狀態,而大學生的 offer 也紛紛被鴿。當時還是Web3行業的牛市,大家把進入Web3行業當成了一個有吸引力的工作選項,但苦於找不到好的學習社區。剛好 SeeDAO 在這時充當了一大批人 Onboarding 進Web3的第一站,大家在這裏相互教學、交友、討論。令我很感動的是,大家還會討論到自己生活中的困境,甚至是談論到自己的抑鬱。我很難想象這些場景會在公司裏發生。而令我很費解的一件事情是,這些人如此優秀,有手有腳,有工作的熱情、能力,也有幫助他人的心,但為什么他們被拋出了社會化協作之外?
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危機時代,我們生活在系統性的失業浪潮中。之前,這個失業的比例可能是 3% ,我們對於那 3% 的人可以不聞不問,認為他們是社會的失敗者。但是,當這個比例擴大到 10% 甚至是 20% 的時候,甚至連我們自己也成為了這些人中的一員時,我們該怎樣看待這些人,看待公司制呢?
我們不妨把這個危機放在一個技術躍進的時代圖景裏。一些人,例如 OpenAI 的創始人 Sam 認為,當越來越智能化的 AI 被投入市場,人類的工作會被大量消滅。他主張給人們發放 UBI,解決失業大軍的生活問題。
但我以為,僅僅發放 UBI 是不夠的。如上面所論證的,工作的意義不僅僅關乎金錢,我們還面臨着失去社會化協作、與社會斷連、實現自我價值的危險。領取 UBI 的生物不是沒有,人類的寵物每天都在喫着我們給他們購买的口糧;有朝一日,人類也許可以每天一邊領 UBI 一邊吸食毒品,或是呆在一個小房間裏孤獨終老。但那是一種悲慘的生活。
人類需要”作“;我們不能只讓公司成為”作“發生的主要形式。我們需要一種為人類所設計,能夠恢復人們的社會連接、鼓勵大家在一起進行社會協作,並在協作中找到自我價值的組織。如今這個時機已經來到。
為人設計的組織
我有一個暴論: 流水线根本不是為人設計的生產流程,而仿照流水线搭建的金字塔式的公司制也絕不是為人設計的組織制度。
很明顯,如果我們的工作環境是流水线式的,每個流水线上的角色都是被定義死,並且要求盡可能控制誤差的,那么人類工作者的效率注定不如機器。自由意志讓人天生就生活在種種偶然之中;在接受控制、服從命令這件事情上,即便是最可靠的人,也不如按照既定程序運作的機器。這一點,在 AI 橫行的時代更加明顯。
AI 驅動的機器人正在替代工廠裏工人們,在我看來這或許並不是壞事——因為這本就不是人的工作以及工作方式。也許若幹年後,當後人回過頭來看我們 20 世紀和 21 世紀的這段歷史,他們會反過頭來嘆息人怎么被安放在了專門為機器所設計的組織系統內,讓無數人的靈魂在這裏消磨,並且還運轉了這樣長的時間。
讓我們思考為人設計的組織。與機器不同的是:首先,人具備心靈,如果所從事的事情違背他的良知或者長期忽視心靈的訴求,他會感到痛苦;其次,人生來有其天性,如果要強行扭曲他的天性要他做某件事情,例如要某個詩人去做流水线工人,其抵抗力會很大,會帶來極大的效率損耗;其三,人是社會動物,需要在社會中通過行動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彰顯自己的意義;最後,我們不應該忘記,為人設計的組織本來就應該以人為目的,而不是一味將人當作實現其他什么目的的工具。
由此看來, 為人設計的組織需要照顧到人的社交需求和自我探索,關注個人在組織內的體驗,而不僅僅是最後的產出結果。
以 SeeDAO 翻譯公會為例:
SeeDAO 翻譯公會是由 200 多個具備Web3翻譯能力的譯者構成的組織,也是華語世界最大的Web3翻譯組織。在 GPT-4 盛行後,公會內部就掀起了是否還需要人工翻譯的討論。堅持結果導向的成員認為,為人工翻譯提供積分激勵已經沒有必要,因為機器翻譯的質量已經超過了不少譯者自身的水平,應該強調選題和校對;而一些喜歡翻譯的譯者則認為,大家加入翻譯公會的原因是喜歡翻譯,並且能從翻譯中學到Web3相關知識。後者說:“機器是能代替我去翻譯一篇文章,但我通過翻譯文章來學會某個概念的過程,卻是無法被替代的呀!”
如果是在公司制下,恐怕老板的選擇就是裁掉譯者,快速搜羅好的選題和校對編輯,提高輸出效率了。然而,在翻譯公會以產出結果導向實驗一段時間後,他們發現活躍的成員越來越少,效率反而降低。逐漸地,大家認識到,大家來到 DAO 內不僅是為了像公司裏的員工那樣產出翻譯稿件的,也是為了自身的成長和同行之間的交流的,不能否認體驗本身的價值。於是,經過投票翻譯公會又回到了人工翻譯,並關注譯者之間交流的路线上。
為人類設計的組織應該關注人的連接和歸屬,並關注人的心靈問題。我們正處於物質極大豐盛的時代,但我們心靈的處境比物質條件不發達的古人更糟。我們被碾成了原子,沒有宗族的照憐,父母關系稀薄,師徒關系幾近斷裂。我們為了金錢遊走在一個又一個公司中,心靈無安定之所,內在的”道“也無法展現。我們生活在他人的地獄中,厭惡與別人過於親密的關系,並且對自己是誰感到深深的疑惑。讓我們感到安全的只有手裏的錢;能讓我們感到”幸福“或”自信“的,往往是消費和對感官的滿足。我們生活在一個又一個嚴密的被技術改造過的系統裏:公司的釘釘、城市的健康碼、老賴不能乘坐的電子高鐵系統……人的行為被規定成了某種可以被量化的數據格式,正常也終於有了一種數據上的標准……
若幹年後我們的子孫再回頭來看,他們也一定覺得十分奇怪:為什么在我們設計了專門為機器准備的系統後,還要把人改造成機器的模樣(腦機接口、賽博格)。“可是我們是作為人而生下來的呀!”
在這種背景下,自由變得十分可疑且虛無。因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閹割心靈,並嘗試把心靈作為威脅系統穩定的一種 bug 和病毒從裏面排除。我們終於完成了一種對人以及對人意義的顛倒。——人已經不是系統的意義;讓這樣一個為機器而設的系統存活下去,成為了系統的意義。
我最近看到了一則新聞,說的是上海某醫院推出了針對抑鬱症患者的腦機接口治療法,其辦法是在患者的腦內放置一個給神經施加電流的裝置,這個裝置可以由手機控制。當患者在手機上選擇开機的時候,神經就得到了電流的刺激,患者也就從沮喪中走了出來,不會想死——當然,他們也知道這不是真正的快樂。這件事情就像現實世界的縮影。在失業大軍與抑鬱大軍如此之多的今天,我們解決不了資本主義的系統問題——盡管這個系統是成批制造抑鬱症的根源,而只能來通過刺激個人的神經來解決自殺問題。這正是現實的可怖之處。
呼喚一個為人而設置的系統,並着手創建這樣一個系統,將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而這樣的系統有一個名稱——DAO(去中心化自組織);有意思的是,它的英文簡寫正是老子所提倡的”道“的拼音。我很樂意把兩者連接起來,甚至”混為一談“。我很樂意說,不能幫助組織內成員更好呈現出他們內在道路和自由的 DAO,不是真正的 DAO。——至多,那只是借着和 DAO 相關的區塊鏈技術,內嵌着公司制的怪胎罷了。
湧現的力量
想象一下幾種事物(我很喜歡觀察它們)的共通性:
-
大海的波濤
-
漩渦
-
雲霧中的大樹
-
冥想後的人
它們的共通性就是湧現。

圖片來自 James Wainscoat on Unsplash
要理解一個為人類而創建的系統,就得理解我們與機器究竟有何不同,就得聊聊湧現的力量。
人來自自然。自然具備生命、能量,以及自我修復的能力。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感到十分驚奇:為什么一棵樹被折斷了枝葉,隨後又可以自己生長;而人造出來的立交橋,當某個橋斷裂了,這個橋無法長出來呢?
有些人會說,因為橋還不算智能。我們可以發明能進行自我維修的機器人。這樣,等他們損壞的時候,這些機器人會自己修自己,它們的手就可以長出來了。
但我認為此事與智能無關。因為一個傻子的頭發掉了,這些頭發也能自己長出來,這種力量內蕴在傻子身上;而機器的手斷了,假使它不去用外部生產的零件修復自己,新的機械手臂也不會白白長出來。我能感受到:“生命”或者“生的力量”來自自然,與智能無關。
我們的身體從自然而來。無論我們多么想成為一個機器人——或者說一個賽博格,但這永遠無法改變我們的“原裝身體”來自自然,它繼承了自然中“生的力量“的事實。自然實在擁有一種偉大的力量。凡來自自然的東西,例如一棵樹、一只貓、一只螞蟻……甚至是大海,它們都具有某種生長和自我修復的能力。這是人造物所不具備的。
作為自然的“造物”,我們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我們生活在某種整體或者關系中。我們的腳下踏着大地,頭頂頂着星空。我們聞着空氣中的氣味,觸摸着肢體所至的實在。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父母鄉親、朋友愛人……我們在自然和社會的網絡中存在着,並用身體在體驗”活着“這件事。而意義和感受則在我們”活着“的過程中湧現了出來。如果我們不再能湧現”意義“和”感受“了,我們就會變成行屍走肉。
自然的造物,仿佛一個彼此連接並不斷湧現的系統。這是對生命的一種描述。當你削掉了湧現的一角,它又开始從這個角开始新的湧現,繼續生長。但如果你把整個系統都破壞掉,這種湧現就停止了——於是,它死了。整體的死亡也預告了局部的死亡,就像一個人死去後,構成我們肢體和細胞也紛紛死去了。
在這樣一個世界裏,人與人所屬整體的其他部分,以及大家所共同構成的這個整體不是命令和被命令的關系,而是一種共在關系。這個世界誠然是不確定的,但卻不是可怖的,因為這種不確定性恰恰是系統內豐富的元素相互影響帶來的結果,就像無數水滴共在的大海總是波濤翻湧。而正是在大海的波濤翻湧中,一滴水確定了自己在波濤的上還是下,在海的中心還是邊緣,在東邊還是南邊……沒有了大海,這些根植於整體的“意義”無從指認,也全部消解掉了。
在這樣的系統中,組織的“效率”與個體的“價值”是合一的,因為個人的價值也是在共在的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如果有明確的“組織”和“個體”的區分的話。但其實,在這樣的世界中,個體反而不會常常感受到那種痛苦的與系統的分離感。他在共在中彰顯出了自我,而不求與共在的割裂與分離,因而反而不會去追求那種只考慮自己的”價值“。(脫離了共在,我們其實無法去指認價值。)
不同的是,在公司中,這種分離感將會非常嚴重。”我只是在給老板打工。“”我是人肉幹電池。“”傻子才對公司掏心掏肺,最後裁員的時候根本沒人記得我。“”不要談感情,給錢就好了。“大家的幸福往往建立在公司之外,例如一個消費的世界:”終於到周末了,我們去哪裏玩好呢?“”我們去买最新款的 LV 包包。“”好开心!我买到了 idol 的最新周邊!“但消費也不是一種直接與人建立連接的方式,它最終讓我們空虛。於是分離無處不在,在分離中對個性的追求無處不在,但這種對個性的追求又時常讓我們發覺自己的軟弱、虛僞與虛無。因為,脫離共在、不需要建立連接、不愿意對生命承擔責任、自言自語的個性其實是一種令人陶醉的幻覺。
我們需要尊重湧現的力量,並重視在湧現過程中隨時與共在連接的感覺。在大多數時候,這是愛和幸福的來源。例如:你腦子中的靈光一閃;突然出現在生命中但讓你覺得眼前一亮的人;心中某種揮之不去的直覺……尊重湧現就是在尊重人自己,因為這正是我們最終的運作方式。
旋渦
漩渦是一種持續不息、不斷卷入參與方並且有明顯能量中心的湧現。
DAO 是一張網絡,但好的 DAO 應該像一個具有生命力的漩渦。而公司則往往像一個層層上漲的金字塔。具有生命力的漩渦意味着,身處漩渦之中的水滴發生了良好的化學反應,能夠自湧不息。

圖片來自 NASA on Unsplash
一個 idea 的形成和真誠的“發愿”很重要,它是漩渦的中心。它往往與創始人相關,但不必綁死這名創始人。漩渦一旦形成,可以從一個地方卷到另一個地方,可以從一個核心人物到另一個甚至一群核心人物。但形成漩渦的中心“力量”要很強大,那股能量不斷吸納、卷入、內化着外部力量,並維持着自身的發展。
被卷入這股漩渦的人,固然是因為那股強大的力量(例如創始人強大的感召力)而來;更重要的是,他們也能在漩渦之中發現和喚醒自己的內在能量。正是他們不斷覺醒的力量,構成了漩渦源源不斷的卷入能量;那些內在能量爆發的點會逐漸成為新的漩渦中心。在 SeeDAO 裏,我已經看到了這樣的一種漩渦中心移動的軌跡:最开始是發起人唐晗,後來是另一個發起人白魚,再後來是 kc、Rebecca、咖啡,再後來是 Shawn,再後來是 Ricky……後面則可能是 Frozen……
中心總在移動,因為中心的能量可能會燃盡,同時別的地方的能量可能會崛起。但是,凡是被卷入過這場漩渦的人,相比起進入漩渦之前,他們的生命狀態確確實實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不是公司制自上而下命令的結果,而是網絡中不同因素相互影響後的表現。這種改變比起公司制來說更加真實,因為它直接指向了參與者個人的生命狀態和意義體悟。
公司制以金錢為激勵,以個人的時間作為燃料,它的能量源在於資本的不斷增值。如果資本無法增值,這個能量源就斷了,人就會慢慢散掉。但 DAO 的能量來源從某種程度上是“憑空”印出來的。它的原理是每個人身上本來就有強大的能量,只是因為沒有在合適的場域被引燃。DAO 的作用是提供一個讓自身能量被引燃的場域,就像把一根木柴放入火堆,在合適的溫度和關系下,這根木柴也會發出光亮。
漩渦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當加入的人越來越多,這些能量很好地協同在一起時,漩渦可能就會變得非常的大,大漩渦的裏面又可能有很多小漩渦。——就像銀河系和太陽系,太陽系和地球的衛星系統。其實 SeeDAO 呈現的狀態已經是這樣了(SeeDAO-公會-公會裏的項目),我覺得這是 DAO 和公司制之間很大的不同。
漩渦一旦形成,就不再能受創始人控制了。——任何企圖控制漩渦的人都會失敗。明智的創始人只能試圖去預測漩渦中心的移動,並在合適的時候對其施加影響。相比起一味提倡去中心化,高喊這個口號相比,我對“漩渦無法被控制”這一點更為滿意。這意味着“去中心化”不再是一個烏托邦的意識形態,而是不得不遵守的治理規律。
我想到了老子在《道德經》裏的所說的“上善若水”。在 DAO 的漩渦裏,順應比控制重要得多。
我想以“白讀書店”為例來闡述我對漩渦的理解,這剛好是我最近一個月所經歷的事情。
大約是在今年的七月份,SeeDAO 的主要成員在重慶討論白皮書的時候,白魚突然提出如果他不做 SeeDAO 的話,他會开一家書店。在活動現場,孫哲鼓勵他直達目的,直接將書店开起來,不要把這件事情放到 SeeDAO 成功以後再做。於是,他便开始鼓動阿豚來做他的書店主理人。
此前,阿豚曾經在成都看到了許多獨立書店,於是白魚便對成都很感興趣。由於我想前往青城山修行,所以也想去成都。最後佳林的朋友臨時改期,因此他接下來有時間空闲,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去成都。 於是我們四人在離开重慶後,便一路西行,相約去了成都。
此時書店還屬於無稽之談,因為白魚根本沒有开書店的經驗,而阿豚也沒有答應做書店主理人。但我很好奇為何白魚對書店一直念念不忘,於是在青羊宮給白魚算了一卦,結果發現這個書店在他生命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於是我一改之前的消極態度,決定將這件事往前推一把。這天晚上,我們在白夜書店遇到了楊熹,而她也處於痛苦的職業變動中,同時也想开一家書店。楊熹是一個建築師,四川人,如果我們找到了店鋪,她可以來做書店的建築設計師,也可以在今年 12 月份辭職後來做書店的主理人。她的出現讓書店看上去靠譜不少。
這天晚上,佳林認領了作書店貓的鏟屎官,而白魚堅定了信心,去寫了書店的白皮書。我們決定給這家書店起名叫”白讀“,英文名叫”white paper“。這天晚上我們對書店信心滿滿。
不過,接下來大家對書店的選址和我們住宿的地理位置處於蒙圈的狀態。書店陷入了停滯。這時候,我們想起了在重慶山上遇到的彥真,她正在川大念研究生,並且也想开一家書店。我們約到了彥真,而她的加入直接幫我們把書店的選址確定在了川大附近,同時我們也確定了集體住在川大附近。彥真在川大念比較文學,還有兩年才畢業,可以來做書店的主理人。
不久,楊熹又拉入了她在成都的音樂人朋友,他也有一個書店夢;彥真則拉來了她的朋友辣椒;SeeDAO 的另一名成員酸奶也加入了進來。整個書店變成了越來越大的漩渦:白魚、我、阿豚、佳林、酸奶、楊熹、彥真、辣椒……書店的選址、建築設計師、建築監工、鏟屎官、主理人、文創設計師、咖啡師漸漸都有了着落。整個書店以比我想象速度要快的方式在成都落地了。
書店落地的整個過程,以白魚起愿為开始,以這個愿望吸引越來越多的加入為過程,我看到了一個漩渦是如何形成的。這個愿望最开始是白魚的愿望,但其實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最後由大家共同建造落地。DAO 的發生和發展,大致也如此吧。
生成式主題,因“作”而“是”
參與者的主體性正是在參與漩渦的運動中生成的。不存在這樣一種身份:公司規定,你是公司的 P 7 級員工,你必須向領導匯報,要討好和對齊,並且必須 996 ……在 DAO 中,你的主體性一开始可能是稀薄的,因為你在漩渦的邊緣。但是,當你越來越深入地被卷入其中;或者,你在漩渦中突然覺醒了自己的力量,對漩渦的運動方向發生了重大作用,這時候你的主體性就被突然加固,或者突然快速生長了。
記住,你始終生活在一張動態變化、運動的網絡中。沒有人能夠決定下一步這張網絡如何,但所有人的參與確實會讓網絡的狀態在下一秒發生改變。此時,你的身份由你自己決定。它在你的個人選擇和網絡的整體運動中步步生成。
我想以 SeeDAO 的成員 Shawn 為例子,講一講我對生成式主體的理解。
Shawn 是在 2022 年 4 月份左右被我拉進 SeeDAO 的。他那時候已經是國內最頂流的 DAO 的 KOL 了,但仍然從 SeeDAO 翻譯公會幹起,一篇文章一篇文章進行翻譯和校對,後來成為了翻譯公會的協調委員,再後來成為了主編。
Shawn 經歷了 SeeDAO 從半公司制半 DAO 制轉向全面 DAO 化的過程,也就是我和白魚解散 CryptoC 這家公司的過程。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十分痛苦的經歷;而在這個過程,他站了出來,成為了起草 SeeDAO 元規則的九人小組成員之一。大家一起總結 SeeDAO 在過去運行中的種種失誤和經驗,並確定了第一版 SeeDAO 元規則。
隨後,SeeDAO 確定了成立與市政廳並列的孵化器,由我、白魚和 Shawn 來作為負責人。孵化器在 SeeDAO 的基礎設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需要處理和平衡好和許多 SeeDAO 核心成員的創業想法,以及他們與 SeeDAO 的關系。這樣的角色,向來不是我所能勝任的,但 Shawn 一直處理得很好。
我只與 Shawn 在大理見過幾次。我們线下相處的時間也寥寥可數。但每次在 SeeDAO 的重要選擇關口,Shawn 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作”確實生成了他在 SeeDAO 的身份,或者說“位置”。
像 Shawn 這樣的人在 SeeDAO 還有不少。從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不同的選擇曲线。我也非常好奇:為什么當一個組織出現問題的時候,是這些人站出來承擔了責任?為什么另外一些人選擇去做了另外一些事情?我們完全可以看到,即便一开始大家加入 SeeDAO 的起點都是一樣的,但隨着個人選擇投入的時間不同、行為不同、作品不同,個人的身份和角色也开始在 SeeDAO 分化發展了。這一點我覺得遠比像 Azuki 和 BAYC 那樣的 NFT 項目有趣,也比 Nouns 這樣由資本驅動的 DAO 有趣。在這些 NFT 項目裏,成員的身份因“买”而“是”,而不是因“作”而“是”。相比起來,SeeDAO 更像一場遊戲(也可以說,人生就像一場遊戲),它為遊戲玩家提供了多種選擇,而每個人的身份也在這些選擇與行動中不斷生成着。
假設你是 SeeDAO 的遊戲玩家,在拿到遊戲账號後,你的身份便在共在中生成,而你可以在其中生成為你想成為的東西:設計師;程序員;治理者;書店主理人;道士。你可以同時有多重身份,也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從事不同的角色。但它們並非毫無關聯。很有可能,當你回過頭來,可以把一連串的身份變動練成一條軌跡,而你正是從這條軌跡中更深得懂得了自己。
我還想以我自己來舉例,這個例子可以更深層次揭示 DAO 的自由:
我想,很多組織的創始人都會最終為組織所累。他們會和這個組織深度綁定,並且將自己的時間精力投入其中,以至於失去了家庭,也沒有時間再去兼顧自己的興趣愛好。我見過不少被Web3異化的創始人,他們最开始可能具備許多的愛好,但慢慢在創業的道路上離最开始的自己越來越遠。
我的終極理想,其實是成為一個語言的魔法師。我生來熱愛語言,文字是我的歸宿。但自從我發起 SeeDAO 後,已經很久沒有再進行真正的寫作了。我為數不多的寫作也變得為這個組織所累。我可能會寫一些和這個組織相關的宣傳文章(例如某個大型的 DAO Conference),但這與我個人的生命體驗無關。
在某個時間段,我曾經陷入了迷茫和痛苦——我發現我找不到 SeeDAO 發起人和我最終理想之間的交集了。我疲倦於無止無盡的對治理的討論以及對人際關系的協調。我發現我在為 SeeDAO 犧牲、消耗。而且在某個時間段裏,我以為這種犧牲是應該的,直到這種犧牲最終完全損耗了我的身體,讓一切變得不可持續。
所幸我踏上了數字遊民的旅途。我本來就是一名記者,又在遊蕩的旅途中積累了許多的見聞,能夠從這些見聞中感受到時代的脈搏。這是我直覺的來源,也成為了後來 SeeDAO 敘事升級的依據。當我走過的地方越多,我收集的故事也越多,重新开始寫作——不只是為了某個組織寫作,這樣的愿望也就越強烈。這種愿望,大概就像是白魚想要开一個書店吧。這也是為什么當我明白書店在他的生命中佔據重要位置時,會義無反顧幫助他的原因。
我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並且是一個隨時准備燃燒自己和犧牲自己的人。抑制自己本來的愿望為一個組織服務,如果這樣就能很多人生活得更好,不辜負他們的期待的話,我是會做出這樣的選擇的。但直到某一天我意識到,如果大家都像我這樣生活,這將是一個令人痛苦的組織。
我开始思考最开始的想法:為何要解散公司,成立一個 DAO?不正是我想找到為人設計的組織嗎?如果連我都不能像人一樣好好生活,這個 DAO 真的能成為一個為人設計的組織嗎?還是說它會變成一個要求每個人背離自己最开始的愿望去犧牲自己的組織?
於是,在旅途中我开始寫與 SeeDAO 毫不相關的遊記。在我卸任 SeeDAO 品牌小組負責人後,這種“毫不相關”更是發揮到了極致。我上武當山調養已經崩潰的身體,在重慶的雲篆山召集开 SeeDAO 的白皮書寫作,又去青城山學習“道醫”。我在探索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卻發現這件事並沒有像我想象的那樣“棄 SeeDAO 於不顧”。無意間,我的行動和選擇也在改變 SeeDAO,改變着大家思考 DAO 的視角。我意識到,成為自己和做一名 DAO 的發起人完全不必對立,這與我做一名公司的創始人完全不同。自此,我完全有信心 DAO 將賦予人們更多自由。不僅是技術上的,而是社會意義上的。
如今,我已經把自己的推特籤名改為了“SeeDAO 發起人,語言魔法師,遊吟詩人”。最終,我在數字遊民的旅途中,找到了語言魔法師和 SeeDAO 發起人的身份的平衡點。
擺脫單個角色的束縛,讓我覺得更自由。這種自由就像是,一顆種子在土地上生根發芽。
生成式主體指向的是一種高級的自由——讓個體內在秩序在整體運動中不斷展开並獲得成就的自由。你不用再“被動犧牲”,被定義為一個單薄的角色了。你不會只有一種遊戲角色。你按照內心的感覺去活、去成就自己。你如此這般是因為你本性就如此這般,它青澀、它成熟,它在一片土地上开花結果,可那是一顆種子自然展开的結果。
沒有什么是事先被允諾的——因為你是什么人的什么人,所以你必須居在什么樣的位置。高官的兒子可以做木匠,而碼農也可以成為一個書店主理人。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真誠的愿望去行動,再從行動中收獲可被認知的身份(這是 SBT,靈魂綁定 token 的可貴之處)。
在我看來,身份是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因為身份連接了個體和整體,確定了人的意義指向。例如,美國人會認為他們為了自由美國,而中國共產黨員會認為他們為了中國人民,密碼朋克們則為了自由的賽博空間。生而為人,你總得為點什么,而不在某個背景下去指認你的價值坐標幾乎是不可能的。就算最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也得指認出自己接下來的行動方向,而行動不可能沒有背景。
我喜歡可以流變的身份,但我不喜歡西方那種口嗨式的“你可以成為你自己”。他們的做法是先定義出許多種身份,再選擇自己屬於什么身份,最後變成了人與人對立的身份政治。這種身份政治是“說”出來的,不是”作“出來的。由於不是在實踐中了解身份,大家很難明白這么多名詞到底有什么意義。語言分割的身份反而固化了身份,只有由行動呈現的流變身份,才能真正反映出生命的真實。
如果要我舉一個例子,我會說:自封為國王不是真正的國王,只有那些行動上承擔了國王責任的才是。真正的女權主義者絕不是沉浸在消費主義裏打拳的人,而是敢於挺身而出承擔責任的女性。
因”作“而”是“,而不是因”稱“而”是“,更不是因“买”而“是”,這是我最喜歡生成式主體的地方。而區塊鏈的功勞是,讓行動在公共账本上留下了痕跡,從而可以以編碼的方式隨時去呈現主體的生成狀態與過程。某種程度上,這解決了名實不符的問題。我們可以行為去觸發獲得 SBT,再以這些 SBT 串聯起我們人生的軌跡。
在 SeeDAO 中,我們已經是這樣在運作的了。但這還不夠,除了單個的行動之外,我們還應該關注人的作品。作品直觀且整體地體現了人的生命狀態,例如一首歌、一部電影、一個項目。靈魂本不該被束縛在數據中。
KPI 該怎么計算:直達目的
我已經在上文中提到了手段和目的的顛倒問題。現在,我想花更多文字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生活在種種顛倒中。語言本來是心靈交流的媒介,為了幫助人更好觸及情境與感受,當你通過語言到達了那個情境,理解了那種感受,語言的梯子就應該被撤掉。但很可惜,我們以語言為真。我們以 GPT 輸出給我們的語言為真,但對身邊動物痛苦的眼神不聞不問。
金錢本來是價值流通的媒介,幫助人們更好生活。但我們現在沒有生活,只要金錢;甚至,我們以一個所謂的“詩與遠方”為賺錢的借口,似乎目標清晰可見,但賺錢的過程卻永無止盡。“當我賺夠了錢我就去寫詩”,但金錢永遠無法滿足,我們永遠在賺錢的路上。我們永遠也無法靠岸。
科技本來是為了探索宇宙的奧祕,並給人類更好的生活體驗。但突然之間,科技發展水平成為了衡量文明發展的尺度。科技淪為了本世紀最大的宗教,誰反對科技發展,誰就是在阻止人類文明進步,誰就是人類文明的罪人——即便科技已經快要置人類於死地。
更不用說 GDP 之於國家發展,考試分數之為學生教育,健康數據之於人體狀態……我們的目的不斷被媒介和手段僭越。
人類總是嘗試給他的目的尋找一條長長的路經,然後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直至方向迷失。
“我還沒有足夠的錢。”“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我不夠理性。”……
最高的效率就是直達目的;如果你還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那最高效的事情就是去尋找自己的方向與目的, 否則會陷入盲目的努力。
在公司制我們往往無法直達目的。但在 DAO 中我們可以。如果在 DAO 中我們還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們又去哪裏做?
如果你想寫詩,你就去寫詩;如果你想給大家分享電影,你就去給大家分享電影;如果你想約什么人一起喫冰淇凌,你就約他一起去喫冰淇凌。直面心靈,付出行動,並承受行動帶來的快樂和痛苦,這是最快的直達目的。
在顛倒的道路上行走的越遠,行走的效率越高,最終也越迷惘。
我建議參與者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評價一個組織的效率:可以先用一個月的時間來考察一個 DAO,再結合自己的自身狀況,寫下自己想要在這個組織內想要完成的愿望清單(例如:找到一個好朋友;學會用 GPT;賺到 1000 塊錢等)。三個月後再回過頭來,看自己寫下的愿望是否實現了,或者是否發生了變化。如果一個愿望也沒實現,那看來你在這個組織中效率低下,或許該考慮離开。
如果你覺得這個組織對你個人有益,可以在三個月後,再審視一下你的人生目標。如果你還沒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可以問自己加入這個組織是否讓你對自己的人生更清晰了;如果你已經有了,可以問自己加入這個組織是否讓你離自己的人生目標更近了。這都是評價一個組織有沒有讓你浪費時間許多生命的方式。
DAO 的競爭:人心
感謝密碼學,也感謝區塊鏈。我們有生之年終於有了這樣一種組織形式:一種不能從物理層面直接消滅的組織形式;或者,一種以暴力手段消滅的成本遠高於讓組織消滅的收益的組織形式。
當一家公司足夠巨大時,這家公司可以輕易擠垮另一家公司,或者吞並另一家公司;但大的 DAO 往往很難幹垮自己的競爭對手。因為 DAO 並不僅僅遵循資本的邏輯,它還遵循社區的邏輯。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人愿意繼承這個 DAO 的歷史,並且愿意為這個 DAO 的存續付出自己的努力,擴大它的共識,這個 DAO 就不會消失。
一家公司的老板可以決定,是否要關停一個公司,或者賣掉一個公司,而且決定的做出往往是出於經濟利益考慮。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個人可以決定是否關停一個 DAO,或者賣掉一個 DAO,除非社區以某種合法機制做出了這樣的決定。然而,即便社區以某種合法機制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例如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表決,贊成票超過二分之一),選擇讓某個 DAO 死去,如果社區中還有人持有反對意見,想要繼承原來 DAO 的歷史,並且在原社區中具備號召力,那么新的社區便可以分叉舊的 DAO。即便社區投票通過決議將 DAO 賣掉,如果买主無法凝聚社會共識(設想孫宇晨購买了某個 DAO),原社區成員又可以很輕易地在社區 KOL 的號召下集合起來形成新的社區,那么收購的意義便會大打折扣。
如果某個 DAO 人心盡失,核心成員不斷出走,並且缺乏新成員的加入和流入,以至於最後沒有人愿意去同步這個 DAO 的歷史账本,那么這個 DAO 就會消亡。因此,DAO 的消亡和延續往往是一個社區內部問題,而不是外部打擊問題。從另一個角度考慮,當內部緊密的情況下,外部打擊可能會不斷強化社區共識,而不是削弱它。如中國古話所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DAO 往往亡於內部治理,而不是外部打擊。
某種意義上,DAO 的本質是人的自由聚集。和公司制不同的地方是,人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加入或者退出一個 DAO。那些無法激發他們的場域,他們可以快速退掉;那些他們不認同的人和理念,沒必要虛僞地附和。人們可以退出一個漩渦,加入另一個漩渦。當某個漩渦的離心力大於向心力時,這個漩渦就慢慢消亡了,或者被別的漩渦喫掉了。這個消亡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暴力的過程。
總之,由於 DAO 是一個跨越地域的組織,所以很難從物理層面徹底消滅它,也很難僅僅以資金鏈斷裂而擠垮它(除非這個組織凝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為了錢);DAO 死亡的唯一原因是沒有人愿意繼承這個組織的歷史,並維持其公共账本。因此,對人心的爭奪將成為 DAO 的主战場。
我期待看到更多基於趣緣的 DAO 的出現,也期待 DAO 之間展开良性競爭,產生更多鼓勵每個人挖掘自己潛能的組織,最後形成美美與共的局面。
對 DAO 工具的思考和展望
最後我想談一談 DAO 工具。
在 2023 年的 DAO HongKong 會議上,我提到過 DAO 和 DAO 工具的相互促進。DAO 必須基於一定的 DAO 工具來展开組織,因此在實踐中 DAO 的組織架構受到了 DAO 工具的制約,而 DAO 的實踐又反過來推動了 DAO 工具的演進。
DAO 的實踐已經有 8 年的歷史了。在 2023 年的 ETH Denver 上,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 DAO 工具,但比較可惜的是,這些 DAO 工具往往不是為一個湧現的系統而設計的,而是將Web2的產品加上區塊鏈的技術改造而成。例如,Web3化的微信、推特、釘釘等。現如今,不僅有不少一體式(涵蓋財務管理、投票和提案系統等)的 DAO 管理工具,還出現了許多的垂類工具。但大家都缺乏用戶。
為了獲得用戶,DAO 工具項目方們設計出了各種各樣的經濟系統,定義出了各種讓大家獲得 token 的行為。然而這似乎並沒有帶來實質意義上的用戶增長,反而助長了羊毛黨的盛行。那些獲得了一线資本投資的 DAO 工具,會有羊毛黨盯着去刷數據,以期在發幣時獲得項目代幣的空投,但他們不是真正的用戶。還有一些項目方,為了獲得真正的用戶,拿出融資款作為獎金,鼓勵用戶去他們的平臺創建 DAO,但效果不如人意。
或許,有生命力的 DAO 根本就不應該是公司制的區塊鏈化?如果項目方按照那些其實沒有太強生命力組織的模樣去打磨工具,那是不是離成功太遠了?也難怪那些最前沿的 DAO 組織都在自研 DAO 工具,例如之前的 BanklessDAO、FWB、Nouns DAO,現在的 Cabin DAO 等。
又或許,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想象一個基於湧現系統而構建的 DAO 工具。我不是說把Web2的產品和管理工具改造後直接變成 DAO 工具都會失敗,但尊重人創造力和生命湧現特性的 DAO 工具似乎更具吸引力。想想看,這樣的 DAO 工具上可能不斷誕生漩渦一般的 DAO,而這樣的 DAO 會席卷更多真實的用戶加入。
我對那些試圖在Web3構建公司制管理工具的產品不太感興趣。我不是產品經理,也不是开發者,而是一個天馬行空的詩人。我想呼喚出一種更具想象力的 DAO 工具:鼓勵創造而不是為了控制,順應生成式主體的需求,並且懂得留白。
要創造出這樣的產品也不能脫離實踐。如今在 SeeDAO,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實踐基礎和需求。就像許多 DAO 工具曾圍繞着 BanklessDAO 和 FWB 被开發出來一樣,希望這樣的 DAO 工具能在 SeeDAO 誕生出來吧。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如有侵權行為,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星球日報
文章數量
9066粉絲數
0
評論